人物简历
台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美国亚里桑那大学教授(1976-),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1988-1990),《食货月刊》执行编辑。曾获得的学术荣誉:中山学术著作奖二次,“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美国华人职业协会杰出奖(1991),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亚裔教授协会教学奖。现职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主要作品
致力于宋辽金史和中国史、边疆史、社会史研究,造诣颇深,具有国际影响。著有:《金海陵帝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边疆史研究集》、《女真史论》、《宋辽关系史研究》、《金世宗的本土运动》、《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中国政治制度中女真统治的影响》、《十二世纪的女真人:汉化研究》等。其中《女真史论》获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学术著作奖,《宋辽关系史研究》2008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比台湾版增加两篇文章。
学思历程
时 间:民国九十年(2001)四月二十四日晚上七时至九时
地 点:国立台湾大学思亮馆国际会议厅
主讲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东吴大学讲座教授陶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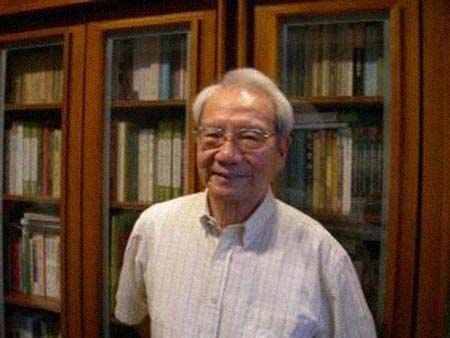
主持人:台大历史系主任高明士教授
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回到母校和大家聚在一起谈谈我的学思历程。我很惭愧,实在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建树,写出来的东西,只有一小撮人知道。我在回国的长途旅程中一直在想,怎样才不辜负邀请我来这里的各位教授、女士和先生、这里的同学对我的期望,怎样才能对大家有一点益处。最近偶然在电视上又看到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野草莓》。从前看这片子时还是研究生,而这次再看这场电影,才能体会到主角的心情。电影的主角是在退休后去领一个学术荣誉,旅途中回想过去,对过去不明了的很多事情,忽然豁然贯通。我在旅途中也有类似的反思。深深感觉昨日之非,却并不觉得今日之是。我出生在大陆,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从香港到桂林,到重庆,我读过五个小学,却没有毕业。从重庆到南京读过两个初中,也没有毕业。一九四九年我家搬到台北。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就读于师大附中高中。那一届共四班,高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以数学成绩分班,我编在十六班,班上共六十人,包括女生。我的数学成绩并不好,比较喜欢国文和历史。那时的兴趣是在文学方面,我从小学时就开始读小说,从《水浒传》、《西游记》、《人猿泰山》、到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初中时开始读中译的外国作品,第一本是《飘》。到高中差不多己把这些译本读完。从小写作文,如果题目是将来的志愿,我从来不想做科学家,而想做文学家。在高中三年,我担任过两年学艺股长,负责学术和艺术方面的工作。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还喜欢绘画和音乐。我从小喜欢音乐,初中时就开始听西洋古典音乐。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学乐器,只好自己学吹口琴。高中时每逢全校办游艺会,同学一定推我出来表演。高一的音乐老师是申学庸老师,我得了八十八分,似乎是全班最高的。高一那年参加壁报比赛,我主编的壁报夺得全台北市第一名,第二年仍是第一。其实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念小学时就办过壁报,父亲取名为《愚报》。是一张不定期、给为家人和邻居看的报,那时大姐读中央大学,大哥读重庆大学,三哥读南开中学,都住沙坪坝。他们回家时就会看我的报。除报导战局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的动态,也有小品文。记得抗战期间物资缺乏,壁报用的是一种深黄色的纸,叫做嘉乐纸。只有抗战胜利出号外,才用白纸红标题:「日本无条件投降」。《愚报》曾于一九四五年带到南京,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离开上海到香港,带到香港。可惜四九年到台湾,却没有带来。在南京念市立一中时,曾经一个人办一张图画壁报。后来在台大参加「融融社」,也办过几期社刊。那时写钢版,用油印机印。附中同学毕业后,只有我一个人考文学院。现在谈一谈大学的学习过程。我于五二年中学毕业,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次年转入历史系。投考外文系的原因,是我从小喜欢看小说,并且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文学家。转系的原因,一方面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研究社会史的先驱,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他的著作。在他的鼓励下,我曾经读过部分的四史。另一方面,大一国文又以《史记》为读本,使我对历史学发生兴趣。我在史次耘师的大一国文班上写的一讨论项羽的作文,得到他的好评,最后一句评语是:「可以读史矣。」在台大前后七年。选过大师和名师的课极多,曾经修过李济师的考古学导论,凌纯声师的地学通论,方东美师的哲学概论,吴相湘师的中国近代史,英千里师的西洋文学史,夏德仪师的中国通史,姚从吾师的辽金元史和历史系规定的必修科史学方法,李宗侗师的中国上古史,牟润孙师的隋唐五代史,劳干师的秦汉史,方豪师的宋史,芮逸夫师的民族学等。还旁听过徐子明、王叔岷、屈万里和全汉升几位老师的课。虽然转到历史系,我的主要兴趣却仍是文学。我曾经试着写小品文和极短篇小说,在联合副刊和晚报上发表,赚点稿费做我的零用钱。对我来说,写小说是眼高手低,所以在大四那年就停止了。不过我对这类文字一直仍有所憧憬。也许因此,几年前我开始写比较通俗的小文章。等一下还要再谈。大学时代的课外活动,主要参加融融社。该社分几组,我或在文艺组,或在音乐组。说到音乐,那时音乐组办唱片欣赏会,是为全校办的。我们借唱机、唱片,写海报,印音乐介绍。一九五六年毕业,随即考入史学研究所。我决定选择历史这一学科,受父亲(陶希圣先生)的鼓励和影响最大。从台大二年级修习辽金元史,到研究所跟随姚从吾师,则是受到姚老师的诱导。姚老师指导我治学的方法,话虽简约,却切中要旨。他指出研究历史必须掌握现存的史料及精读史料,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寻找新史料。同时要熟悉国内外研究成果,也就是他所谓的「行情」。于是我大量阅读宋金史料,如宋辽金三史,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些文集和笔记小说。本来准备写宋金关系中的宋高宗,后来考虑到这个题目也许会牵涉到台湾偏安一隅的政局,就改从宋金关系方面来找题目。在姚老师的德国式的研究班上读史料及练习写报告,颇有心得。后来的硕士论文论述宋金间之采石战役。一九五九年毕业。在研究所时,选修芮逸夫老师的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课程则使我对这个学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我觉得文化人类学对于研究边疆民族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大学毕业后,考入史学研究所,因此没有立即入伍受预备军官的训练。一九五九年研究所毕业后,才以抽签的方式接受空军行政官的磨炼。一九六一年结束,一时无处可去,幸得姚老师的帮助,与李敖同作姚老师的国家讲座研究助理半年。受军训期间,已经知道没有在大学固定工作的机会,于是有出国的想法。因为当时国外研究辽金元史的学者以日本学者为多,也最著名,因此与京都大学的田村实造教授连络。不过,到日本去必须完全自费,所以也申请美国的三所大学,居然得到了美国印第安那大学亚洲研究的奖学金,入历史学系。虽然没有去日本,和田村先生还是有连络。后来为他的颂寿论文集写过一篇短文。一九六一年秋天,远渡重洋。乘飞机抵达美国西岸后,从旧金山乘灰狗巴士三天三夜,抵达印第安那州布露明顿的印第安那大学,从邓嗣禹教授攻读。邓师为学严谨,极为用功,每天都在学校研究室里工作,时常晚上也在。他对学生的要求和督促极严格,虽然他专精近代史,对我的研究却非常注意和督导,要求我遍读我研究工作必须精读和参考的史料,和现代学者的有关书籍,如拉铁摩尔和卫特福格等的著作。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也时时督导,并且注意和我论文有关的论著与史科。读历史博士必须于主修的中国史和东亚史外,另有两个主要范围和一门系外学科。我的两个范围是美国外交史和欧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系外选文化人类学。我对这个学科特别有兴趣,一共选修了十二个学分。教美国外交史的法勒尔(Robert Ferrell)教授著作等身,他传授外交史上的知识,对我后来的工作颇有启发。此外,在我的英文写作方面,他指点我文笔简要平顺,给我很大的鼓励。于一九六七年获博士学位。在印大的几年,可说非常用功,每天必定在图书馆看书到午夜,周末也不例外。因为读英文速度比美国人差,唯有这样才能赶得上他们。而且想超越他们,就自己多看规定之外的书。到了学期快结束时,更是紧张,为了赶写学期报告,或研究论文,或预备大考,有时两天不睡觉。有一阵子每晚打字到天亮,鸟鸣然后睡觉。博士论文以金代女真的汉化为题,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在写博士论文期间,回国一年,执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其后三年任教于密西根州卡拉马助(Kalamazoo)的西密西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历史学系,并于一九六七年完成博士论文。现在来谈一谈我的教学和研究。这个历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九六六年至六九年是一个较短的阶段,以完成博士论文和教学为主,完成博士论文算是学生时代的结束。一九六九年至七六年在台湾,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期间教学极忙,但是主要的工作是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以必须做出成绩来。此外又主办《食货月刊》,疲于奔命。一九七六年至今在国外,是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工作刚开始,而且一面教书,一面写论文。西密大前身是师范学院,并不特别重视研究。学生包括不少的中学教员,因此有夜间和星期六上午的课程。由于我是新的助理教授,必须多教书,不像较大的学校对新任的助理教授有种种优待。加以和初在美国教书,深感教学工作繁重,第一年每学期教十一个小时,包括夜间和周六上午各一节课。历史系里每个教授必需开一年级的两门课之一,西方文明史或美国史。我选择西方文明史。三年里教过的课程很多,包括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远东现代史、西方文明史,和中国史研究 (历史系授硕士学往)。当时正值越战期间,选远东现代史的学生颇多,有一年需要开两班,每班七十人。西密大没有中文书,所以时常开车到七十哩外的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图书馆去看书和借书。在西密大教书时深以没有时间做研究为苦。一九六九年,经芮逸夫老师的推荐,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属于历史组。并在台湾大学历史系合聘。又曾在师大研究所兼教过一门课。这是我在学术界的第二个阶段的开始。一九七一年姚从吾师逝世,我继姚师讲授辽金元史,及研究所硕士班必修的课程「研究实习」。早在一九六五年,系主任许倬云兄己经把这门课交给我,这门课让我认识了很多杰出的年轻朋友。互相切磋。这几年中和同学一起讨论,深得教学相长的乐趣和益处。在史语所的几年经常和同事们谈论,并参加每两周举办一次的讲论会。每位研究人员每年必须将研究成果在讲论会上提出来,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才能将所提论文修改后发表。这样的互相切磋和互相批评的制度,使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因此发表的论文,错误就比较少。我的历史研究趋向,在研究所时期一方面受了姚老师的教诲,脚踏实地的读史书和史料;另一方面受父亲研究社会史和芮逸夫师研究民族学的影响,觉得历史不仅要了解材科,选择材料,组织材料,还要解释。姚师和父亲都相信历史学当属于社会学科,可以作科学的研究。姚师留学德国多年,接受兰克和班海穆的观念,甚至把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提并论。在这种影下,我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因此在台大教书时和编《食货月刊》时,提倡参考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法来启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和发掘问题。我在研究实习班上曾经邀请社会科学家来介绍他们的学科,尤其着重这些学科和史学的关系,或这些学科对史学研究会有什么启发或贡献。来班上谈这些问题的朋友有文崇一、张存武、李亦园、胡佛、杨国枢、丁邦新、袁颂西、于宗先、易君博、瞿海源等,颇引起一些同学的兴趣。一九七四年食货月刊社和思与言杂志社联合举行「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座谈会。我在那次座谈会这样说:有人说,史家所据以作判断的只是常识而已。但是现代社会科学家的发现,使常识的层次提高。史家要转向他们来充实自己的常识,不应墨守过去的陈腔滥调。所谓陈腔滥调,指「暴政必亡」,或比较流行的「人们有了较宽裕的生活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于是乎就发生革命」(所谓“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s”)这一类的泛泛之论。那时候写的两三篇论文颇采取一些社会科学的观念(因所知有限,谈不上理论)。例如上述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分析金世宗的本土运动。对北宋初期的党争,并不觉得毫无积极的贡献,反而觉得不同意见的激荡,有时会产生等思广益的效果。也就是说,冲突并不见得没有积极的意义。就这一点来说,我的看法毕竟受了当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接受社会冲突也有积极贡献的说法。另一方面,一九七〇年代正是党外人士要求民主开放,和革新保台人士要求当政者广开言路,切实改革的时候。这种要求自然会和当权者发生冲突,冲突固然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正面的贡献较多。我研究历史的范围,从大学时代到任教于亚里桑那大学后的十年间,以辽金史、宋辽和宋金关系史为主。我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七六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于一九七八年在台出版。这本书讨论女真人的汉化,认为金代女真人进入华北后,虽然曾经一度迫使汉人女真化,也一度力图恢复女真文化,但是由于居于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入主华北后,不免采取汉人的制度来统治,同时若干人也开始采取汉人的语言文字,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了语言和习俗。尤其是和汉人通婚后,主要的趋势是在社会的层面,两个族群整合;在文化的层面是受到汉文化的涵化。写这篇论文参考了当时的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一些观念,如涵化(acculturation)。说到民族的融合,必须讨论汉化或华化的问题。共其实这个问题既是贯穿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和现代有密切的关系。汉化或华化是当汉民族和另一个民族接触时,这另一个民族放弃了自身的族群认同及其文化,而与汉民族通婚,采取了汉文化。应当强调的一点是,汉化或华化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里,汉化的程度与另一个时期不同。而且当汉化发生后,并不是说被汉化的民族文化完全消失。根据这个定义,让我们来观察契丹,女真和蒙古的汉化。首先,契丹族的汉化程度,在辽朝一代,可以说相当粗浅。辽朝的统治阶层里,有若干贵族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例如以汉文作文及吟诗。不过,基本上很多契丹平民在契丹人实施的两元制度下,仍旧过着游牧的生活方式。而移居到汉人居住的燕云地区的契丹人则受到了较多的汉文化的影响。辽朝末期,一部分契丹人西迁,建立了西辽。留在华北的族人则开始和女真族和汉族融合。契丹族真正的汉化,应当是金朝灭亡后的事。金末元初的耶律铸和耶律楚材父子都和汉族文人没有甚么差别。到了元代,元朝政府将华北的契丹人,女真人,和汉人一律称为汉人,就是契丹人终于已经汉化的有力的证据。非汉族建立朝代后,居于少数的统治族群在过去王朝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上,建立了新的上层社会阶级。有的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初期企图维持本族文化与社会制度,甚至企图同化汉人。如女真族占领华北后,一度迫使汉人改换女真服装和发式,并且禁止族际通婚。金世宗努力恢复女真族的原有的风俗。这种本土运动失败后,很多女真人就大量的采取汉人的制度和风俗。有的外来的统治者如元代的蒙古人则对汉人的制度和文化作有限度的借取。不过,非汉族朝代的文化终于会受到汉文化的冲击。汉族人口上的优势和统治族群对族际通婚限制的放松促进了对少数民族的涵化和同化的趋势。换言之,游牧民族对汉人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影响是有相当多的族人被汉族所同化,加入中原汉族的社会而成为汉族社会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族人抗拒同化。如金代的金世宗企图恢复女真族的固有文化。对于女真统治者的这种政策,我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 或movement of revival)的观点来分析,和一般认为金世宗主张汉化的观点不同。不过,金代中期的本土运动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接受了汉文化。蒙古民族在元代的汉化程度则远不如金代的女真族。明代建立的过程中,若干蒙古族人向北迁移而脱离了汉族的社会。目前在美国有一些汉学家研究所谓「征服王朝」,认为「汉化」一词不妥。如包弼德( Peter Bol)在他讨论金代汉人知识分子的文章里,不用「汉化」,而用所谓「文」(即他对「文明」,civilization的中文翻译)。可是,女真人「文明化」的来源仍然是汉文化。以「文」来代替「汉化」也不见得更细致(subtle)。 至于清代,近来也有人认为清代的满洲统治族群中有一些人相当成功的保留了满族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主张今后不必用汉化的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看法引起了辩论。由于很多西方史学家基本上不同意中国历来认为夷狄都被汉人同化的说法,这本书出版后,自然曾经引起一些争论。不过,几年前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六册,也就是辽,金,元三代的历史,对金代女真族的汉化,认为程度超过辽和元两代。即使有人仍然认为多数外来民族被汉人社会吸收,还是需要注意当两个文化接触时,其间发生的是互动而不是单向的流动和影响。传统和目前多数的中国和台港的史家,一般都认为中国历史上汉族总是能够吸收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大陆的史家甚至反对把这些民族看作外族,认为他们都是汉族的兄弟民族,其间的冲突只是兄弟间的内哄。这种看法显然与政治环境有关。总之,汉化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一九七二年助父亲将一九三O年代著名的《食货半月刊》在台北复刊,改为月刊。我负责约稿、编辑、送印刷厂、送作者初校、自己二校、甚至用油印机自印订阅者地址、将刊物装封套、邮寄等等,一手包办了四年之久。我还得不时写些小稿补白。忙得不亦乐乎。《食货月刊》一共办了十七年,我出国后主要由黄宽重、沈松侨等几位热心的朋友接办。这本刊物表了很多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论文和书评,也介绍了颇多涉及史学和社会科学关系的著作。虽然《食货月刊》介绍和提倡社会科学的观念和方方法,但是重点还是在基于史料的实证研究。当然我在这段历程中也增长了见识。食货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一九八八年父亲病重时,决定把杂志停刊。朋友们觉得可惜,就集资创办《新史学》。因为只有我不是公职人员,所以由我来登记,担任社长。一九七六年《金代女真的汉化》英文版问世,同时我转到国外工作,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其实在这之前我己经研究宋辽关系两三年,利用各种史料,详细分析探讨北宋对辽的政策和外交,辽朝对宋的政策,宋、辽、西夏、和高丽国际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宋人力求国际上势力的均衡。一九八三年出版《宋辽关系史研究》。在这本书里,我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提出多元国际关系的看法。在写作的过程中,相当巧合的一件事是被素不相识的罗沙比(Morris Rossabi)教授邀请参加十至十四世纪东亚的多元国际关系的研讨会。为这次会议我提出的论文讨论宋人对辽的看法。后来收入《宋辽关系史研究》。这本书的英文版于一九八八年出版。得到颇多好评。有一篇书评说本书是「分析任何时期中国外交和政治史有价值的模型。」一九七八年至七九年我回史语所和台大一年。当时所长高去寻先生要我提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画,目的在执行这个计画时可以增加研究人员。我对他说,我还是要在国外工作,不便主持计画,但是他认为没有问题。于是我就提出一个研究从唐末五代到元朝的社会变迁的计画,经费六百万元。果然因为这个计画的关系,增加了参与研究工作的人员。也由于主持这个计画,我开始转入北宋社会史的领域,于是开始了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我对士大夫家族的历史特别有兴趣。在这方面,我决心把北宋有关士大夫家族的史料通盘检查一遍,包括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诸家文集、笔记小说、地方志、诗词、碑志、以及族谱。为了收集族谱资料,曾经两度到犹他州盐湖城的家族图书馆去看族谱,前后一个月。写《北宋士族》这本书,以传记资料为主,也就是文集中和考古发现的墓志,希望从撰写碑志的士人的笔下所描述的士人们的所作所为中,来观察他们的实际生活。写法是一种相当传统的方式,可以说不过是将史料割裂后,重新加以组织和堆积,谈不上什么理论。这本书讨论北宋扩大考试制度,很多新兴士人进入政府。为了维持家族谜继续兴盛,发展了一些策略,包括与其他士族通婚,聚书、延师,经营产业等。研究士族,当然要研究士族妇女,于是也收集妇女方面的资料。书中有三章讨论妇女的生活、教育、婚姻,尤其是再嫁、改嫁的问题。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从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认识到史料的确实存在。当我们发现了一块石刻的材料,如墓志。而现存文集中也存在这篇文章,比对的结果,也许相差几个字,也许一个字也不差。这时的感觉,就是历史事实有确切的存在。另一方面,在处理史料时,又体会到史料不会说话。研究者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后,史料才帮助研究者说话。但是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常会刻意以资料来证明他的想法或理论,而是研究者和资料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研究者在选择材料和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当然是主观的加以取舍。历史研究能够客观吗?我觉得很难做到客观,研究历史的人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而已。以上提到的第二种感想,令我对历史研究的看法有所改变。其实这种改变并不是受了所谓后现代的影响,而是从实际工作里体会到的。早在我提倡参考社会学的观念和理论时,也涉猎一些史学方法方面的著作。对于克罗齐(Croce)和卡耳(E.H.Carr)等的看法有些了解。在我写宋辽外交关系史那本书时,只参考了政治学方面的决策模式来讨论外交关系。宋辽之间的关系,不论将来有什么新资料出现,大致的轮廓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对于宋辽之间关系的解释,则因时代的变迁,就会出现新的见解,例如宋方的两个与政策的制定很关键的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邓广铭先生对他们就有前后不同的看法。又例如对金海陵王的评价,在八十年代大陆改革开放时,有人说海陵王是改革家。当然这种看法也和海陵王企图以武力统一天下有关。到了写宋代士人和士大夫家族的这本书时,虽然大致利用了少数的社会科学的常识,却没有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我对于七、八十年代西方史学研究的趋势略有所知,但是教学工作限制了深入的了解。当然实际上有时间也不可能遍览群籍。一个历史研究者总不能跟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跑,而且即使能够勉强跟上时代,还存在着西方学术理论能否运用到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因此写北宋士族的过程中,对这本书的写法很有一番思考,后来决定把理论放在一边,埋头组织材料和写作。(其实把理论放在一边并不表示心中没有主见或想法。) 写成后觉得很不满意,因为范围太广。再者,书中好几章都是为参加会议而写的,前后几年中,想法写和写法不免有所差异。但总觉得写史书虽不能客观,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是得继续努力。还有一件事要稍微谈一下。学术和社会是有各种关系的,书写得好,读的人多,可以把所学供众人参考。书教得好,学生得到益处,不论学生将来是否留在学术界,仍都有影响。除此之外,我在做研究时,常会感觉困惑,究竟写这些学术性的书,这些文章,对社会文化,究竟有何作用?尤其这些作品的读者少得可怜,我的贡献和社会对我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惟一的比较通俗的书是《中国近古史》。有了这样的困惑,于是几年前开始写过去的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用比较通俗的笔法来写。主要想法是抓住历史上的一个瞬间,来反映这个人物,或这个历史事件。希望透过这种方式为社会提供一点服务。一九七六应美国亚里桑那大学之聘,任教于东方研究系(后改称东亚研究系)。在亚里桑那大学曾担任系主任一年(一九八七),其后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两年(一九八八至九O)。并曾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客座教授(一九八三),研究讲座(一九九八)。在亚里桑那大学,每学期教两门课。教过的课程有中国通史、上古史、隋唐至元代史、传统中国史研究、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史、汉学方法。在亚大教过和指导博士论文的年轻朋友则多半来自台湾。总结来说,从一九五六年进台大历史研究所,开始做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达四十五年之久。教书从一九六五年至今也有三十六年。一生中只是研究和教书。我的经验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研究是长期的工作,尤其研究中国的悠久历史,留下浩瀚的史籍和资料,更要一点一滴的去找寻,去累集。其实,从事任何研究工作,要下定决心去投入,要锲而不舍。不论做哪一类的研究,一方面要有兴趣去做,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另一方面要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我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汉族与边疆民族之间的文化关系;传统中国的外交和东亚的国际关系;近世中国社会的形成。另一点经验是,很多年轻人在大学时还没有决定到底是否要做学术研究。也许决心做某种研究工作的时候,有一点晚。苏老泉(苏洵)不是到了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吗?我自己到进了台大研究所才开始用功。但因大学时代分数不很高,影响到拿了硕士却没有教职。出国时已经二十八岁。念英文念得甚苦,但还是不会比美国同学差;后来在美国教书,研究方面的成绩,在系里可说是最好的。这就是下工夫的结果。最后一点,在学术界工作的人,尤其像我们在人文学科工作的人,我们的成绩说起来好像颇出色,但是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的人,就是在我们同一行业少数的人。所以我们时时应当反省究竟我为大家做了什么。这是我的反省,也许对同学们有一点勉励的意思。
问答阶段
问:请问为什么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历史研究比较投入?第二,刚才您提到要去北京开会,谈小脚跟歌妓关系的研究,可否请老师要多讲述您这方面的内容。第三,您对于现今的大学生有何建议?如果让您重新来过的话,您觉得可以加强那方面?答:日本文化因为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要研究中国。此外是由于他们在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企图,当时日本已经控制东北,他们有一本书叫做异民族支那统治史,尤其是对满蒙对中国的统治有很深研究,所以他们研究中国历史可以说与政治环境有关,而且研究的成果也非常好。我为了要谈小脚跟歌妓的关系,看了很多北宋的资料,包括很多诗词方面的文献。宋朝的士大夫在中进士之后都会举行宴会,所以有些士大夫会自己养歌妓,也写了很多诗词来描写当时的情形。其实从这些资料里面可以发现,这些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除了看歌舞表演之外,还会看这个女孩子是不是长的够漂亮,他们的舞姿、手势、容貌等等。从南唐后主开始有缠小脚的歌妓表演之后,后来也普及到酒楼及士大夫家族之中,虽然我有这方面的研究,可是我对于一个问题却无法解决,就是当时的歌妓、舞妓看起来是一种比较下层的职业,可是为什么这些士大夫会因为欣赏小脚而让家里的女子也开始缠小脚,这样不就等于同流合污了吗?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决,也无法解决。尤其写词的人都会写这些歌舞女郎多么美艳动人,但是他们都不会写到自己的妻子,他们往往惊叹歌舞女郎的脚小,那是不是代表他们的妻子脚非常大,甚至是天足,然后演变到最后为什么这些女子也开始缠脚,这是我看到的一个现象,但我至今还没有答案。大学应不应该用功?当然应该用功。大学生活是多采多姿的,所以别的事情也要参加,除了上课以外,去听演讲、跟别人讨论、参加社团活动都是很重要的。我在大学时也参加社团,我们常常举办活动,例如读书会、音乐欣赏会等等。高主任明士:我对于同学的第一个问题稍做补充。日本的学术研究除了民族感情因素之外,我可以再提出三点供同学做参考:第一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学术研究都没有断过,而反观我们从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断断续续的,从民国39年到现在,我们的学问可以说是从头做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跟当初唐朝日本人来中国留学相较之下,真的会非常沮丧。第二是我在东大的时候,我曾经问我的同学以后会不会到美国留学,他们都没有意愿,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最新的知识马上就会介绍到日本国内,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去留学。第三是他们做学问非常扎实,我们的毛病是大而化之,目前来讲顶级的注解或注释都是日本人做的,包括大陆现在出版的都不如日本,而日本人一步一步扎实的去做,事实上背后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我提出这三点给同学做参考。问:陶教授刚才提到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对于少数民族的问题,中国基本上强调的是同化,而美国强调的是民族大融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成公主下嫁西藏,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也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以历史的角度来看,未来假如这些少数民族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机会,那么他们会比较希望跟中国汉族在一起,或者会有很强的独立意识?第二,陶教授刚才提到美国学生对中国历史比较没有兴趣,这是否因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民族习性不够了解,导致学生产生冲突。而中国从近代史多被侵略,也使得中国人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在此情形之下,中美两国未来是会走向合作或是对抗?第三,请问陶教授有没有修过傅故校长的课,或者就陶教授对傅故校长的了解,提出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答:关于边疆民族跟少数民族政策方面,假如中国走向更民主的话,当然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会更好。现今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多是跟美国学习,例如让少数民族可以生两个小孩,不受一胎化政策的影响;有方语教育等等,不过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他们必须要这么做,至于将来是否会走向独立,就美国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而言,美国是不会允许少数民族脱离他们而独立的。第二个问题,我想学历史的人没有办法预测将来会如何,不过我想应该是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从前阵子的撞机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大陆还是有些克制,虽然美国在布希上台之后政策有所改变,也感觉比较自傲,使得现今冲突好像变多,但我想这是会过去的。目前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不要搧动民族情绪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第三,我没有机会上到傅斯年校长的课,对于他在史语所的学术地位以及领导方式我们都很了解,我们对他非常敬重,他是很开阔,胸境很宽大的一个人,也非常用的去提拔后进。关于傅校长个人的风格,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可以叫出学生的名字。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史语所方面,在社会史论战期间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看历史,当时他是不同意的,他强调的是一分证据讲一分话。傅斯年校长对于历史研究还是重视科学,认为历史就是一种有新的资料才可以做出问题来,他创造出另一种学风,当然他的影响没有三十年代马克思盛行的那个情形,不过他对台湾的学术界是影响很大的。注释:《食货月刊》,四卷,页377-378。 参考S.N.Eisenstad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书中指出北宋时代的党争有正面的价值,明清政局远不如北宋。 涵化与同化的分别, 参看George E. Possetta, ed., Assimilation, Accultur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1. 此书中分辨涵化与汉化 。前者指文化的采借(如语言),后者指民族藉通婚而同化。此种分别始自 Milton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根据这种定义,可以知道美国黑人几乎完全涵化于白人文化中,而并没有经由黑白通婚而达到同化。黑人与白人的通婚仍在同化的过程中。 “Seeking Common Ground: Han Literati under Jurchen Rul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7, No.2 (1987), pp. 461-538. 参看Evelyn S. Rawski,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4(1996), pp. 829-850. Ping-ti Ho,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1(1998), pp. 123-155.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history of any period.” Kathryn M. Lynduff, review in Asian Perspectives, I (1988-89),p.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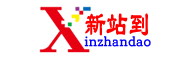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徐国华(教授) 简历 - 名人简历
徐国华(教授) 简历 - 名人简历 刘玉春(将领) 简历 - 名人简历
刘玉春(将领) 简历 - 名人简历 范斌(教练) 简历 - 名人简历
范斌(教练) 简历 - 名人简历 李清照介绍 李清照的诗词全集 李清照最
李清照介绍 李清照的诗词全集 李清照最 山东有哪些著名的词人 济南二安占尽了千古
山东有哪些著名的词人 济南二安占尽了千古 婉约派八大词人排名,看看你最欣赏的词人排
婉约派八大词人排名,看看你最欣赏的词人排 彭元植 简历 - 名人简历
彭元植 简历 - 名人简历 姚刚(演员) 简历 - 名人简历
姚刚(演员) 简历 - 名人简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