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只要是明星,都自带吸粉技能,在唐朝,尤以为甚。生前便有吴筠、、等一线巨星追捧,死后更是粉丝无数,骄傲的文艺青年(hù)就是其中一个。
张祜有诗才,却不愿当书呆子,便自诩为诗酒风流的少年侠客。于是,张祜的侠义名声逐渐传开。
一个深夜,张祜正在挑灯修改新作。一腰悬长剑的大汉推门而入,手中提了一个沉甸甸带血迹的麻袋。见了张祜便说道:“今日我手刃苦苦寻找了十年的仇人,割下了他的首级,刚好路过此地,想跟兄弟讨一杯酒喝。”
张祜二话不说,陪大汉一起饮酒。几杯酒下肚之后,那人又说:“我听江湖上说,张侠士您十分讲义气,我想向您借十万串钱,去报答约距此地三五里外的一位恩人,去去就回,如侠士愿意帮我完成夙愿,我誓将一生追随侠士,任您使唤!”
张祜听大汉这么说,心想:原来江湖上早有哥的传说!不禁飘飘然。遂起身掏出几乎全部积蓄,送予大汉。大汉将那麻袋往墙角一丢,出门而去,还嘱咐张祜不要睡,等他回来一起嗨。
张祜目送大汉的身影消失在茫茫月色之中,便继续去推敲新作。不知不觉,张祜抬头看窗外发白,快天亮了,还不见大汉回来。
张祜暗觉不妙,这屋子里可还有一个人头啊!赶忙起身去看墙角的麻袋,当他颤颤惊惊打开口袋,一个毛都没刮脏兮兮的猪头映入眼帘。
张祜不禁大呼一口气,恐惧的心瞬间失落不已:你大爷的啊,被骗了!
张祜遭此欺骗,气愤至极。次日,他一边嚼着猪头肉,一边自我安慰:“也罢也罢!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好歹还落下一个猪头。”
只是,这一个猪头便耗费了张祜十万串钱,也太贵了。自此,张祜不再谈行侠仗义之事,但性格,依旧放荡不羁。
2
看到张祜被骗,你要以为他只是个憨头憨脑的二愣子,那可就是天大的误会了!他的真实身份是“张公子”,是古代顶尖望族清河张氏后人。
张祜少年时,客居在如诗如的苏州城,自身天赋,加上受家风熏陶,年纪轻轻便享有才子的美名。
张祜十八岁那年,他听说宣武军代理节度使陆长源为其部下所杀,而且被煮熟吃掉,十分悲痛愤慨,写了一首《哭汴(biàn)州陆大夫诗》,对陆长源的惨死表示哀悼,一时流传甚广。
但除了喜欢伸张正义,张祜表现更多的是放荡不羁的一面。
张祜最喜欢的事情,是时不时约一帮好友到杭州、扬州等地旅游,大把青春,肆意挥霍。要么夜宿于青楼,要么对酒吟诗。
他那首脍炙人口的《纵游淮南》,开创了除“花下死”的另一种“死法”: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
扬州,实在是风流名士的绝佳去处,怪不得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张祜后来回忆那段放浪的少年生活说: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
嗜酒几曾群众小,为人多是讽诸侯。
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
今朝更有憔悴意,不堪风月满扬州。
一个不愁吃不愁喝的豪门二代,对个人前途这事,不大在意。一直到近40岁,张祜也仅在徐州节度使李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等人幕下混了小段时间。其余时间四处游历名山大川,行踪飘忽不定。
还好,由于文人圈不时传出张祜的佳作,江湖上依然有他的传说。彼时,在朝廷做宰相的令狐楚,很是欣赏张祜。就喊话张祜:“选300篇你自认为不错的作品来长安,老夫推荐你入朝做官!”
天降横运,张祜心想:这么些年哥也玩厌了,入朝做官也不错。于是整理旧作汇编成册,便直往首都长安而去。
令狐楚拿到张祜的作品集后,亲自写推荐信给唐宪宗:“张祜从小就刻苦钻研文章,在文艺界成名已久,他的文章自成风格,比一般人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我让他准备这些文稿,进献给圣上,希望允许让张祜在中书省效力。”
令狐楚对张祜绝对是真爱!要知道,张祜不过是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平头老百姓。而中书省是朝廷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起草诏令,其部门长官即是当朝掌握实权的宰相之一。如进了中书省,就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权力的中心。
3
这时,唐宪宗为了顾及当朝另一位宰相、文坛大佬的感受,便叫元稹发表下看法,原意是走一个过场。
不料,元稹很郑重地对宪宗说:“张祜的文章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如果陛下破格提拔,恐怕对我朝的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张祜这小辫子,元稹其实抓得很准。张祜虽为一介平民,却对前朝的宫闱秘事很感兴趣,写过很多宫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作),请看他最有名的一首《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
据说,在唐武宗即将病逝之际,身边有一位才貌俱佳的才人日夜侍奉。一日,唐武宗对才人说:“我时日无多了,如果我走了,你该怎么办啊!”
才人心伤不已,答道:“假如陛下离我而去,我也不会苟活在人间。”说完,她为唐武宗唱了张祜这首宫词,凄惨悱恻,哀痛不已,一曲未终,肠断而亡。
此外,张祜还写了不少“宫廷八卦”诗。如八卦杨玉环与唐玄宗的哥哥李宪有私情的《宁哥来》、描写虢国夫人的《集灵台二首》、描写马嵬之变《马嵬坡》……
在流传下来的近40首宫词中,张祜对李唐家族的皇室感情、生活、后宫之事,发挥了充分而大胆的想象,尽情挪揄。
所以,当元稹“提醒”唐宪宗注意社会影响时,唐宪宗立马想到了张祜那些“有损皇室威严”的诗句来,便打消了让张祜进入中央的念头。
其实,元稹以此抵制张祜,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真实原因,是元稹与令狐楚分属不同的政治派系,两系之间一直明争暗斗,积怨颇深。推荐张祜入朝,在元稹看来,就是令狐楚想培养心腹党羽,自然要加以制止。
这些事,张祜一无所知。他在长安一呆便是三年,从开始的踌躇满志,到中间的彷徨煎熬,再到后来依旧杳无音讯,他终于明白了。
转而,张祜想到了曲线救国——找有名望的地方官推荐入仕,走“地方包围中央”的战略。
于是,张祜前往杭州,他要找的,是杭州刺史、大诗人。张祜在拜访白居易时,恰逢浙江才子徐凝也在场。相较张祜,白居易似乎对徐凝更赏识,便将解元(省级考试第一名)给了徐凝,张祜又空手而归。
可张祜应该会明白,白居易是元稹的好基友,他们在文学的主张上也十分相似,为了文学改革,一起开展了“新乐府运动”,推荐你张祜?这辈子都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张祜还拜访过不少文坛前辈,可惜均无功而返。也许那些文坛前辈早有所耳闻:张祜差点进了中央,被皇上亲自压下来了!
张祜有点郁闷,他在《偶题》一诗里说,像李白那么癫狂的人,都幸运地遇见了伯乐贺知章,可惜我虽有李白之才,却没有遇到我的伯乐。
自此之后,张祜的政治热情彻底熄灭。官场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收拾收拾心情,张祜又开始了他的漂泊之旅。
4
在唐朝比较知名的诗人中,一生都没吃过国家俸禄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另一个,就是张祜了。
对于读书人来说,半辈子都在写诗,却没弄个一官半职,实在很不“成功学”。
罢了罢了!张祜离开杭州,在苏浙一带游山玩水,此时的张祜,经济条件也不似年轻时那么好了,时常很拮据,但并没有影响他生活的闲情逸致。
当张祜来到江苏丹阳后,被深深的吸引,决定不再漂泊。张祜在此造起房子,还在房子四周种上了蔬菜、树木、竹子,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这一住,光阴不知不觉又溜走好多年。
还好,身为一介平民的张祜,究竟还有知音,这知音便是比他小二十岁的风流才子杜牧。早在杜牧担任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推官时,就结识了来扬州游玩的张祜,两位才子,一样风流,一样不顺,自是惺惺相惜。
但就像许多老朋友一样,十几年间,分隔不同的地方,也都各有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机会把酒叙旧。
张祜近60岁时,得知杜牧要到安徽出任池州刺史,开心极了,许久没有出游的他,乘船溯而上,去拜访这位忘年之交。
在途中,张祜已提前写了一封信寄给杜牧,杜牧兴奋不已,天天念叨这位许久未曾谋面的前辈,好不容易把张祜给盼来了!
杜牧准备了丰盛的酒菜,还叫上许多陪客,为远道而来的张祜接风洗尘。席间,一众人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张祜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
那几日,杜牧将繁忙的公务放下,陪张祜游览池州美景,一起谈心论诗。对于张祜这位诗坛前辈,杜牧是很尊敬的。所以,一向自视甚高的杜牧,将自己的旧作翻出来,请张祜指点。张祜特别喜欢杜牧那首《》,还兴致勃勃写了一首《读池州杜员外杜秋娘》。
在闲谈中,张祜向杜牧说起了杭州见白居易那件往事,杜牧愤慨不已。杜牧本就对元稹、白居易这两人搞出的“新乐府运动”颇不感冒,现在又听说自己一向敬重的张大哥竟然曾被白居易压制,再看看张祜如今年过花甲一无所有,惋惜之余十分不爽。
在后来两人登池州九峰楼时,杜牧作了一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候。
在诗中,杜牧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气,将垂垂老矣的文坛巨臂白老前辈狠狠讽刺了一番,说白居易“目不见睫有眼无珠”,还认为万户侯,都不如张祜的一千首佳作。
孰是孰非,早已无对错之分。难能可贵的是,杜牧以刺史身份,为了一个平头老百姓朋友,敢公开讽刺白居易这位在当时就名满天下的“诗王”,实在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胆量,也让人对他们之间这种感慨不已。
相较于杜牧的愤慨,张祜早已看开了。他在《和杜使君九华楼见寄》的结尾中说道:“杜陵归去春应早,莫厌青山谢眺家。 ”
大意是说,算了吧,这些往事就不提了,让我们忘记那些陈年的恩怨,一切向前看。
张祜一日比一日老了,他有一些想回老家看看。满怀着激动地心情,张祜踏上了返乡的路程。听闻当年的豪门子弟回来,乡亲们还是好奇的,纷纷前来迎接。
然而,当他们看到张公子一事无成,立马从好奇变成了无情的嘲讽。还好,见惯大风大浪的张祜,依旧只是用自嘲来安慰自己:
行却江南路几千,归来不把一文钱。
乡人笑我穷寒鬼,还似襄阳孟浩然。
相比年轻时常拿李白自比,而中年之后的张祜,则常以孟浩然自居,而时人也多认为张祜跟孟浩然的境遇差不多。张祜曾经不远千里,到襄阳瞻仰了孟浩然的故居,并写下:
高才何必贵,下位不妨贤。
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
好像是对孟浩然的称赞,也好像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安慰,但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张祜自身的写照。一生未名未禄又何妨?一生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又何妨?人性的高贵,无法以拥有的财富衡量;人自身的价值,也无法以社会地位衡量。毕竟,追求过,奋斗过,用心用情生活过,便不负那短暂而平淡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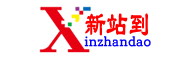 新站到V网_Xinzhandao.COM
新站到V网_Xinzhandao.COM 宁夏朝觐报名网登录入口https://w
宁夏朝觐报名网登录入口https://w 石家庄人民政府官网受理查询平台入口111
石家庄人民政府官网受理查询平台入口111 2023年石家庄中考报名系统121.28
2023年石家庄中考报名系统121.28 江苏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www.j
江苏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www.j 文心一言官网yiyan.baidu.co
文心一言官网yiyan.baidu.co 温州英特流向信息查询系统www.wzme
温州英特流向信息查询系统www.wzme 青海省朝觐报名网站登录入口http://
青海省朝觐报名网站登录入口http:// 2023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m
2023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