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现,
含有“最是”二字的,
似乎带有一种魔力,
它总让人在平平淡淡的阅读中,
毫无察觉地走进诗人的灵魂深处,
并与之产生强烈的共鸣。
蝶恋花·阅尽天涯苦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如许。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离别是一个悲剧,归来还是一个悲剧。静安词的悲剧色彩之特别浓厚,正表现在这些地方。人间的分离,无论是生命的自然终结,抑或是客观环境的阻碍,都构成永恒的苦恼。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正)是橙黄橘绿时。
虽有“傲霜枝”,终究还是要退出初冬的舞台,难道大自然就注定要走向衰败了吗?当然不是,请你放眼大自然,不是还能看到黄黄的橙子、绿绿的橘子吗?此时,橙橘飘香,青黄杂糅,生机盎然,别有一种风情。因此,诗人满怀欣喜地提醒刘景文,一年之中最美好的春光正是橙黄橘绿的初冬时节啊。
·曲阑深处重相见
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
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
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檀痕涴。
忆来何事最销魂,第一折技花样罗裙。
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生离”还有一丝重逢的希望,而“死别”则是硬生生地将希望在你眼前撕碎。纳兰与妻子生死相隔,凄楚半生,仍不忘旧日深情,特别是在月明之夜,形单影只,最让人黯然销魂。纳兰是一个不懂得节制的人,有点像,一悲就是悲到底,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承受折磨,“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
野 步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秋风和春风都是大自然的创造者,春风将万物唤醒,而秋风则使万物凋零。秋风萧萧地吹,吹红了枫叶,同时也吹白了人的满头乌发,更吹走了似水流年。
这里的秋风,不再仅限于秋风,还代表了整个,代表了无情流逝的时间。岁月流逝,使枫叶变红,也使人的头发变白。诗人将对时间的埋怨,化为对秋风的嗔怪,虽然有悖情理,却也深婉动人,易引起读者共鸣:谁的青春不是这么无情地流逝?今朝,当秋风吹来的时候,镜里的朱颜已经不同于昨天。
台 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当年的台城,十里长堤,杨柳堆烟,何等繁华热闹,如今,台城长满了野草,只有亘古如斯的依旧若无其事地生长着。
它不管历史如何沧桑巨变,更不管人世朝代的兴亡荣辱,只是“依旧烟笼十里堤”,所以,台城柳是最“无情”的。
少年游·离多最是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
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
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今番同。
离别和碰上薄情人,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痛苦。离别毕竟不是死别·,总有相会的时候。水往低处流,尽管千回百转,东西异向,而最终会汇流一处——“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
此词以自然和人事相对比,用无情之物比有情之人,表达情人离别之苦和相思之怨。
临江仙·寒柳
纳兰性德
飞絮飞花何处是, 层冰积雪摧残。
疏疏一树五更寒。
爱他明月好, 憔悴也相关。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
湔裙梦断续应难。
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
越是繁华过后的清冷收场,越加地令人回忆起往事的美好。当年约会的情形是那样的清晰,仿佛还在昨天,而如今断缘难续,就连奢侈的梦中相见都是如此遥不可及。
破阵子
李煜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从一国之主沦为“臣虏”,无异于从天堂跌落到地狱,这种人生落差世上有几人能承受得住?对李煜这种纯真任纵之人来说,更是如此。他像一样变得憔悴,像潘岳一样年纪轻轻就生白发,这所有的变化,均源于亡国之痛。最让人悲痛的是什么?“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尤其是在拜别祖先的那天,本就羞愧难当伤心欲绝,偏偏又听到教坊里演奏别离的曲子。词人再难以承受,不禁“垂泪对宫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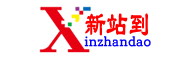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宁夏朝觐报名网登录入口https://w
宁夏朝觐报名网登录入口https://w 石家庄人民政府官网受理查询平台入口111
石家庄人民政府官网受理查询平台入口111 2023年石家庄中考报名系统121.28
2023年石家庄中考报名系统121.28 江苏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www.j
江苏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www.j 文心一言官网yiyan.baidu.co
文心一言官网yiyan.baidu.co 温州英特流向信息查询系统www.wzme
温州英特流向信息查询系统www.wzme 青海省朝觐报名网站登录入口http://
青海省朝觐报名网站登录入口http:// 2023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m
2023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