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的诗,杜公给人的印象是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穷困潦倒的人设形象。
其实不尽然,杜甫在梓州期间,曾经多次参与陪游玩、陪吃喝、陪观艳舞的“三陪”活动。并写出了几首反映这些活动的“三陪”诗,其中包括两首陪喝花酒、陪观艳舞这类题材的艳诗。正是这些极为罕见的“另类”艳诗,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梓州地方官的生活奢靡腐败,是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丽人行》等帝王及朝廷显贵腐败生活链的延伸和补充。
公元762年7月,奉诏入朝,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叛,成都动乱。杜甫在严武举荐下来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避乱。
大唐盛世,梓州作为当时与成都齐名的大都会,朝廷大员、相邻各州、梓州所属各县官员以及诗友往来等,自然不会少。设宴办招待是梓州州官应尽的地主之谊。曾在朝廷当过小吏、嗜酒如命却又诗才横溢的杜甫,便是出席这种场合的最佳人选,被梓州最高军政长官李訔看好,被安排去赴宴陪上一赔。
(一)陪游玩
梓州以及州属各县,名胜风景颇多,杜甫来此半年不到,闲得无聊的他,业已把这些景点游的差不多了。陪游,是李大人的安排,杜甫也不便推辞,接受任务便是。《陪李王苏李四使君登惠义寺》一诗,除了描写惠义寺(今琴泉寺)的“虚空”幽静外,被陪的四人只字未提。诗人表达的主观感受无非是“迟暮身何得,登临意惘然”的失意,以及“谁能解金印,潇洒共安禅”那种篱下的自我安慰。
除了陪游,杜甫在梓州还参加了陪吃陪喝活动。他在梓州写下160多首诗,其中描写陪吃陪喝参与公款迎来送往的诗就有20余首,这还不包括杜甫应邀去通泉、射洪、盐亭等州属各县喝酒写的诗。
(二)喝花酒
在欣赏杜公艳诗之前,我们先看看当时梓州地方官的HomeParty(私人聚会)吧。杜诗中有的一首《戏题恼郝使君兄》的诗,记载的是杜甫应邀去梓州所辖的通泉(今进射洪沱牌镇)县一个姓郝的使君家中做客的故事。
席中,登徒子郝某居然使出常见的招数:以妓佐酒,旨在显摆。“愿携王赵两红颜,再聘肌肤如素练”。他唤出家妓——姓王和姓赵的两位红颜,入席为自己夹菜、斟酒。
这让杜甫很是不爽,于是以戏题的口吻讽刺道:“通泉百里近梓州,请公一来开我愁”。意思是,你有朝一日不妨携两位红颜,到百里之外的梓州来,让我也解解愁啊。
尽管郝使君是杜甫的好友,杜甫吃了人家的口不软,照样讥讽不误,只不过以“戏题”二字封住渣男郝某人的嘴,让他没有还口之由罢了。
私宴如是,那么当时公款接待的Party又是怎样一番景况呢?《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这首艳诗,写的便是一帮梓州地方官东渡涪江,登顶东山喝花酒的故事。杜公这首艳诗原文是:
姚公美政谁与俦?不减昔时陈太丘。
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骢马游。
东山高顶罗珍馐,下顾城郭解我忧。
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彩舟。
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
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
三更风起寒浪涌,听取喧呼觉船重。
满空星河光破碎,四座宾客色不动。
请公深临莫相违,回船罢酒上马归。
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
这首艳诗的前四句,先夸姚县令“美政”可比肩当年太丘县令陈实,继称多日骑马闲游梓州的王侍御(侍御,伺候皇帝的人)为“上客”。
接下来四句,先用“珍馐”二字说明宴会档次高,接着写酒宴时间之长---饮至太阳落山。这顿酒少说也有五六个小时吧?这么长的时间里,光是故事佐酒吗?那多没意思。况且哪有么多故事?格子哥以为,席间可能安排有其它活动——并且是有趣的活动。虽然杜公诗中没有描述,但码字君以为,极有可能是大家都感兴趣的。
(三)行酒令
大唐盛世,流行“以妓佐酒”。
这里的“妓”,指的是“饮妓”,也就是陪酒女。陪酒女中的佼佼者叫做“酒纠”或“席纠”,相当于现在的活动主持人,是一场酒筵中的具体组织者,在唐代中后期多由女性担任。成为“酒纠”的女子容貌佳、酒量大、善交际、善言词、能歌舞。因此,行酒令大多由“酒纠”担纲主持。
唐代的酒令文化风靡一时。《》卷二八六《张和》记载,德宗初贞元年,张和赴盛盛,装扮华美,有盛装打扮的妓女(饮妓)陪酒。酒筵中行闪球之令,即行抛球酒令(类似当今社会的传花游戏)。玩这种酒令在当时十分新颖、有趣和流行。唐代诗人李宣古也在参加酒筵中观摩了“酒纠”崔云娘带领诸客行抛打令的场景,并作《咏崔云娘》诗云:“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啸出歌迟。”
为何会“抛令急”呢?如果接到邻座抛来的球,在手中停留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间,就要被罚酒。除了抛球令外,绕口令、掷骰子等也是当时酒宴上常用的以酒为乐、消磨时光的有趣活动。
不管此次宴席上开启的是哪一种酒令模式,抑或是多种模式兼具,想必此次东山宴姚通泉,席上男人大多喝过“罚酒”吧?就这样行乐喝花酒,一直喝到日暮黄昏,方才“复携美人登彩舟”。一个“复”字,表明宴会上这些陪酒佳丽和歌舞艺妓,是从涪江西岸登上彩舟过江登上东山的,此时宴毕下山再次登上彩舟。
这是要回家的节奏吗?NO!
(四)观艳舞
“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涪江上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这彩舟之上的歌舞厅,莫非是水上青楼?抑或是官妓活动会所?因为史无记载,我们暂且不论。
嘹亮的笛声婉转悠扬,艺妓们踏歌而舞,队形逶迤起伏。乐队乐师们的演奏也太精彩了,以至于水中的鱼儿都要浮出水面来聆听,“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这些大鱼,仿佛知音,听得懂曲中所表达的情感。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歌声时而动人,像潺潺流水般浅吟低唱,独具风韵;时而凄美,若珠落玉盘,扣人心弦,耐人寻味。船上听众或已沉醉其中,有不枉此生的感觉吧?
船上,艳舞笙歌,节目一个接一个。近距离观艳舞的男人们在干嘛呢?喝酒呀!但喝酒这个细节,被杜公巧妙地隐藏在诗的标题中——“晚携酒泛江”。
天哪,白天一个下午还没喝够,晚上继续操练。有权就是这么任性,有酒就是这么刺激。
红巾翠袖,艳舞天籁,推杯换盏。既饱口福,又饱眼福,且饮切观且珍惜。时至”满空星河光破碎”,这帮饮男才恋恋不舍地“回船罢酒上马归”。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梓州饮界大咖们,喝了十几个小时的花酒,居然“四座宾客色不动”---脸色没有变动(意即无醉意),吃酒战打成了持久战,“不倒翁”们居然还能够骑马回家,不愧是“酒精考验”的酒色双痴。你看这花酒喝的,还能找着回家的路吗?
赴宴作陪,杜公的味蕾跟着李大当家沾光,“腐败”一回算一回。没办法,彼时的杜甫已没有了官职俸禄,若非朝中严武罩着,全家在梓州恐怕要喝西北风了。无可奈何地蹭吃蹭喝并且将在以后继续蹭的他,已经没有当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锋芒毕露,只是在艳诗的末尾,从关心宾主健康的角度,委婉劝诫道:“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旨在希望这些地方官在追求声色娱乐之时,要有所节制,不可过度放纵,当心乐极生悲。用诗说话的杜甫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适者生存”罢了。
金壶盛酒歌舞升平,且饮且观且珍惜。
如果说上面这首艳诗反映的是梓州地方官喝花酒时间最长一次的话,那么,下面这首艳诗表现的则是歌舞侍酒美女阵容最为强大的一次。
从唐代起,文人士大夫聚会饮筵,时兴招妓女(指歌妓而非色妓),由酒纠行令佐酒,或以歌舞侍宴。梓州政坛大当家李訔是个资深的艳舞的爱好者,曾多次安排艺妓们在大船上表演艳舞,让杜甫作陪。《数陪李梓州泛江有乐女在诸舫二首》这样写道:
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
江青歌扇底,旷野舞衣前。
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
兢将明媚色,偷看艳阳天。
白日移歌袖,凌霄近笛床
翠眉萦度曲,云鬓俨分行。
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
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
这首描写陪梓州李大人观艳舞的艳诗。前四句描写李訔大白天骑马来到梓州城东的涪江边,让马儿返空回府。舞女们舞动扇子,倩影倒映在清澈的江水之中。“诸舫”(几艘大船)容不下太多的舞女,剩下的只好在空旷的岸上翩翩起舞。
这是何等庞大的演出阵容啊?快赶上长安城里的皇家歌舞团了!你李訔也太奢侈了吧?
“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的描写更是精彩。舞女们跳舞的动作,让大船失去平衡,让手提“金壶”斟酒的“饮妓”左右摇晃,涪江上的波浪都“偏”(不正常)了。
哇塞!好你个李梓州,敢用金壶盛酒,这哪是一般的嘚瑟,这是超高调的炫耀啊!皇宫亦不过如此吧?
接下来的“兢将明媚色,偷看艳阳天”这句,生动动的描写了舞女中几个“马叉虫”朝着李大人频抛眉眼、暗送秋波的暧昧一幕。看来,李梓州也是个登徒子,莫非暗中跟那几个“马叉虫”舞女有一腿吧?
“白日移歌袖,凌霄近笛床”。日光已经斜照在歌妓们的衣袖上了,竹笛演奏的曲子响彻云霄,曼妙的舞姿逶迤起伏。各位“观众老爷”看得如痴如醉,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
“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前来接各位“老爷”回府的马儿站立在岸边时,已经是暮色笼罩群山,歌女们卸妆洗面后,一川江水都被脂粉染香了。这场规模宏大的酒池肉林,喝的用的,得花费多少银子啊?
无奈寄人篱下讨生活、一饱眼福后的诗人只能用诗歌把当时官场的奢华场面这一事实展示出来。尾联,他并没有就这般挥金如土的腐败现象进行评说,而是笔锋一转,以歌女们对李大人眉来眼去为实锤,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规劝道:你李訔可是个有家室的人,饱饱眼福也就罢了,你可别突破道德底线,去学野鸳鸯的不端苟合行为哈。
“艳舞”一词,在唐代仅仅指着装艳丽的年轻女子所跳的舞。其外延并不包括今天的暴露狂舞蹈、甚至裸舞。艳舞始于宫廷,盛于地方。当年就在宫中观看过艳舞,写下了《宫中行乐词八首》。“艳舞全如巧,娇歌半欲休”是其名句。
杜甫这首写观艳舞的诗,把李訔这个好色之徒刻得入木三分:他已多次观赏艳舞并享受媚眼秋波但意犹未尽,以至于“三更风起寒浪涌”也在所不惜!
话题回到“三陪”上来。当时梓州官方迎来送往,让杜甫当“三陪翁”,杜公并不反感,有邀必至。在他看来,迎来送往,吃饭喝酒很正常,是待客礼数。
(五)官员们喝花酒观艳舞,杜甫为什么没有在艳诗中对其进行谴责呢?
唐朝是一个“美女经济”蓬勃发展的朝代。北宋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唐人尚文好狎。”当时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还是官员们聚会游玩,都要以妓乐助兴。官吏文人士大夫宿娼狎妓盛行。出任杭州刺史时常携妓游玩;《》对一代才女坠入乐籍及其入蜀后在韦皋幕府中大红大紫也有记载。此外,官僚贵族们还普遍蓄养家妓。对此,朝廷法纪并无禁令。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去蜀》)。鉴于当时那样的社会风气,杜公在两首艳诗中非但没有对喝花酒观艳舞本身予以抨击,而且自己还多次应邀作陪积极参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他当时无非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罢了。
其实,他不对地方官们毫无节制的奢靡行为进行谴责,也是有苦衷的。这在他后来即将离开梓州的一首《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中可见一斑:“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我最近将要辞别梓州这帮特别能喝酒的家伙,再也不甘打折自己的气节而落在很多有气节的人后面。显然,杜甫对梓州官府的醉生梦死和过度奢靡的行径怒而不言,仅仅是暂时的“折节”,缘由则是前述观点“适者生存”---为生存而去被动适应。如此而已。
人非圣贤,孰能无瑕?在杜甫一生将近60个春秋的人生旅途中,这种无奈的“三陪”,毕竟是极少数。试想如果没有杜甫去“三陪”,他能写出那些弥足珍贵的艳诗吗?如果没有那些艳诗,我们能够了解到梓州那些“痛饮徒”鱼肉百姓、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吗?显然都不可能。应该说,这些“三陪诗”,丝毫无损于他忠君、爱国、爱家、忧民的“伟光正”人设,相反,通过这些艳诗,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血肉丰满的真实杜甫,一个热爱生活、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道德底线的诗人,一个敢作敢当、敢于曝光他人,也敢于揭短自己敢讲真话且光明磊落的正直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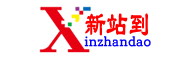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宁夏朝觐报名网登录入口https://w
宁夏朝觐报名网登录入口https://w 石家庄人民政府官网受理查询平台入口111
石家庄人民政府官网受理查询平台入口111 2023年石家庄中考报名系统121.28
2023年石家庄中考报名系统121.28 江苏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www.j
江苏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系统www.j 文心一言官网yiyan.baidu.co
文心一言官网yiyan.baidu.co 温州英特流向信息查询系统www.wzme
温州英特流向信息查询系统www.wzme 青海省朝觐报名网站登录入口http://
青海省朝觐报名网站登录入口http:// 2023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m
2023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m